|
中国古都学会的任务,不仅是要研究我国古代都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还要研究作为文化遗产的都城遗址,在当前城市发展中如何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现实问题。本次学会年会重点开展城市文化建设学术研究,对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进行研讨,是我国古都学研究内容的一次非常重要的扩展我非常赞成,并撰写本文予以支持。
最近,媒体不断报道大同市长耿彦波在城市建设中保护文化遗产的先进事迹,使我联想到洛阳近半个世纪來,在城市发展进程中文化遗产保护所走过的艰难里程,使我想起了郑振铎、夏鼐等逝去的先生,也想起了许多为保护文化遗产作出贡献的人们。
洛阳是我国著名的古都、历史文化名城,享有“九朝古都”之誉。洛阳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定为我国的重工业城市,国家在这里就建有拖拉机机、轴承厂、铜加工厂、柴油机厂、矿山机械厂、玻璃厂等十几座重工业工厂,于是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城市在洛阳拨地而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洛阳已拥有城市建成面积105平方公里,成为我国的一个著名的较大城市。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对矛盾,由于历史的原因,现洛阳市区已覆盖了整个东周王城(东周时期都城)和大半个隋唐洛阳城(隋唐时期都城),所以洛阳市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的保护矛盾尤为尖锐,我们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为此做出了不少的努力。本文仅就发生在古都洛阳的几件事,说明在城市化的初期阶段和加速阶段,文化遗产面临着的损毁和严重损毁,保护是何等地艰难,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一)
20世纪5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百业待兴。我国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以苏联援建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兴起了建国以来第一个建设高潮。在这156个项目中,在洛阳工业区兴建的有6个,这就是中国政府1953年5月至1954年10月间与苏联政府签署的多个援助协议中的拖拉机厂、轴承厂、矿山机械厂、热电厂、铜加工厂和高速柴油机制造厂。所以当时古都洛阳的文化遗产保护,就面临着工厂选址和洛阳市第一期城市发展总体规划的考验。
1953年7月15日,有一机部、建工部和地方政府参与,以中国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建厂筹备处为主,重型矿山机械厂筹备处参加,成立联合选厂组。筹备处根据一机部汽车局的意见,主要在洛阳老城西郊的西工地区洛河以北,面积约10平方公里范围内选址。筹备处认为这片地区地形开阔平坦,地下水位低,土质好,居民少,靠近城市,铁道接轨方便,经济上比较合理。筹备处在征得地方政府同意后,由筹备处北京工作组组长崔维亭负责到国务院各部办理审批手续。1953年9月初,崔维亭带领几个精兵强将,按照有关规定,到一机部、民政部、财政部、民航局、铁道部等部门汇报,一路顺利过关,只在铁道部为陇海铁路接轨费了一点周折,最后也通过了。崔维亭回到住处,心里很高兴,心想只剩下一个文化部了,文化部与新建工厂关系不大,明天让下面同志去一下就行了。没有想到,文化部坚决不同意,说这里是周王城遗址,不能建厂。崔维亭得知,非常意外,说:“我去,我就不相信文化部有多少理由能否定在这里建厂。”第二天,他带领原班人马来到文化部,见到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先生。听崔维亭等陈述了在西工区建厂的理由后,郑振铎局长不紧不慢的说:“你们要在洛阳涧河东边建工厂是不行的,郭(郭沫若)老也不会同意,因为在那里,地下有周王城的遗迹,是无价之宝。”崔维亭不服气地问:“郑局长,几千年的事了,你怎么知道?”郑振铎搬出有关资料,做了详细的解释。随后,郑振铎局长上报了文化部的的意见並得到了国务院(当时称政务院)领导支持。1953年10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郑振铎起草的《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其中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央、省(市)级工矿、交通、水利及其他基本建设的主管部门,在较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程确定施工路线、施工地区之前,应负责与同级文化主管部门联系,必要时应即商订工地保护文物工作的具体办法,认真执行。地方文化主管部门不能决定时,得报请中央文化部决定,商由基本建设主管部门在预定工地,先期进行勘查钻探,再行决定施工。各部门如在重要古遗址地区,如西安、咸阳、洛阳、龙门、安阳、云岗等地区进行基本建设,必须会同中央文化部与中国科学院研究保护、保存或清理的办法。中央文化部认为必须在这些地区的指定地点避免进行基本建设工程时,可会商有关部门呈报政务院批准。”筹备处因此放弃在此处建厂。
1953年9月,建工部城市规划局成立洛阳城市规划组,开始洛阳城市规划的准备工作。1954年初,洛阳市成立城市建设委员会,下设规划处,负责洛阳城市规划工作。
1954年4月,建工部城市规划局洛阳城市规划组13人来到洛阳,与洛阳市城市建设委员会规划处的30余人一起,在指导专家、苏联列宁格勒国家城市设计院建筑师巴拉金的参与下,共同进行洛阳城市规划。1954年8月份,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把西工区作为城市的中心区,涧西和老城各设一个副中心,形成东西长15公里,南北宽平均3公里的带状形格局。在西工区规划中,将铁路以南、洛潼公路以北(即拖拉机厂最初选择的厂址)作为工业保留区。1954年11月13日,洛阳涧西工业区初步规划,在国家建设委员会主持,国家计委、一机部、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卫生部、铁道部、水利部、公安部负责人和河南省、洛阳市领导参加的审查会上,被批准通过。1956年上半年,洛阳市在1954年初步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涧东暨城市总体规划,1956年7月,洛阳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向河南省、洛阳市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一致同意。随后,在国家建设委员会主持,文化部、卫生部、公安部、国家城市建设总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审查会上,洛阳市第一期规划被批准通过。
郑振铎先生和梁思成先生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奠基者。1950年,建筑学家梁思成、陈占祥先生,以“古今兼顾、新旧两利”发展城市的理念为主导,联名提出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避开明清北京城,选址旧城西郊月坛至公主坟之间的“梁、陈方案”,和1953年郑振铎先生不同意洛阳拖拉机厂在东周王城遗址上建厂,都是体现了城市建设避开不可移动文化遗产以整体保护文化遗产的思想和理念。不过我想说明的是,现在规划界、文物界把“远离旧城建新城”的正确处理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模式,即城市建设“洛阳模式”的桂冠,授之于洛阳市第一期城市发展规划,实际上是把20世纪50年代初期前后发生的“拖厂选址”与洛阳第一期城市发展总体规划混淆在一起了。现在我们剥开历史的迷雾,把洛阳拖拉机厂的选址与洛阳市第一期总体规划的制定分割开来,并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洛阳拖拉机厂原来选址西工区被否定,就是因为西工区地下埋藏有东周王城(后来考古发现西工区还埋藏有同样重要的隋唐东都城遗址),其历史功绩应归于郑振铎先生;而紧跟其后发生的洛阳市第一期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却又把西工区规划为城市中心。在这块文物埋藏异常丰富的东周、隋唐都城遗址上建设现代化的洛阳市中心,这与在此处建设拖拉机厂又有什么区别?这不是对原来拖拉机厂选址西工区否定的否定又是什么?1966年,在原來拖拉机选址的西工区兴建起两个大厂,洛玻璃厂和洛阳棉纺织厂,现在,经过50多年来洛阳城市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中心已出现在西工区,覆盖了整个东周王城遗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半个隋唐东都城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使郑振铎先生生前保护东周王城遗址的努力变成了泡影。面对东周王城与隋唐东都城宫城、皇城、东城遗址毁灭性的破坏,寻根溯源,不正是洛阳市第一期城市总体规划的错误造成又是什么?可以讲,洛阳市第一期总体规划为东周王城与隋唐东都城,在洛阳城市化进程中遭受毁灭性破坏,提供了规划依据。
(二)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城市化迅猛推进的年代,洛阳城市建设步伐明显加快。洛阳市城市建设向洛河南岸的意图越来越清楚。1992年,菲律宾籍华裔巨商郑宗敏先生访问洛阳,与洛阳市签订合作协议,在洛河南岸购地20平方公里,扬言在洛阳南岸再建一个洛阳城。洛阳市城市规划部门奉命在洛河南岸进行总体规划,当时的洛阳市领导的确是信心十足,雄心勃勃。
1992年夏天,洛阳市土地管理规划局局长王伯辉约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叶万松与洛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文物科长段哓宝,征求意见。他说,郑氏集团征地建设的事,市里催得很急,洛阳规划部门淮备将古城村一带共4个平方公里,作为第一批土地出让,你们看怎么样?叶万松和段晓宝表示不同意,因为这4个平方公里正位于隋唐东都城的保护范围内。叶万松先生说:“由于50年代第一期城市总体规划的失误,把西工区作为城市中心来规划,最终导至洛河以北的整个东周王城与半个隋唐东都城被现代化城市占用,占地47平方公里隋唐城现在只剩下洛河南岸这20多平方公里了。如果今天郑周敏来占4个平方公里,明天必然有张周敏、李周敏来占另外的四个、五个平方公里。那么,用不了多少时间,隋唐东都城洛南的这20平方公里里坊遗址也会被现代化城市吞没。这样的话,不仅是东周王城遗址,而且连著称于世的整个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隋唐东都城遗址,都是被我的这一俩代人在短短的几十年间从地球上抹掉了。也许现在我们许多人还意识不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那么再过50年,一个世纪,人们又会怎样来评价我们这些现代人的行为呢,这个历史责任又让谁来承担?!所以希望决策者在这个涉及到民族利益、历史文化遗产的重大问题上,一定要慎重再慎重。”王伯辉局长很为赞同,并积极向市领导汇报。于是市领导暂时放弃了首批出让隋唐东都城4个平方公里土地方案。
隋唐东都洛阳城面临着被现代化城市完全吞没的危险。叶万松先生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隋唐东都洛阳城洛河南岸里坊遗址区(20平方公里)绿地保护的构想。他到处宣传他的主张,逐渐地为洛阳市规划部门、市部分领导、中央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一些专家、学者接受。洛阳市规划部门在1992年底经过反复慎重研究之后,提出了洛河南岸城市规划一定要避开隋唐里坊遗址,至少是2000年以前不考虑遗址保护范围内的建设用地问题,这个规划意见便成了洛阳市第三期城市发展总体规划中最为关健且最具特色的内容。
1995年8月,在省建设厅主持和中央建设部的参与下,洛阳市召开了洛阳市第三期城市发展总体规划论证会,与会者来自全国各地规划界的权威专家和中央文物考古界的专家。规划论证会高度评价规划方案提出的“隋唐城洛南里坊区不作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规划意见。认为洛阳市第三期城市发展总体规划突出了隋唐东都城遗址的保护,是本期规划的关键性成果和本期规划的成功之处。
1996年,叶万松奉命主持编制隋唐洛阳城保护规划的工作。作为考古专家的叶万松、李德方先生和城市规划专家的李国恩先生联名在《文物与考古》1996年第3期发表了《隋唐洛阳城的考古发现与文物保护》,阐述了隋唐洛阳城保护规划的宗旨和具体规划设想。这个由洛阳市文物工作队、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考古专家和洛阳市土地规划局规划专家组成的编制小组,五年里反复研究,四易其稿,全面阐述了他们对隋唐洛阳城里坊遗址绿地保护的构想。
保护规划方案指出:洛南里坊区绿地保护的近期目标是,隋唐洛阳城洛河南岸20平方公里“不作城市建设用地,维持现状。以保护地下文物遗迹为目的,辟为绿地保护区域。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住宅开发、工厂建设,不得增建、扩建或改建任何永久性建筑和城市道路;不得在该区及该区的城墙附近烧砖、冶炼及化工生产等破坏遗址、污染环境的产业;不得在该区内进行取土活动,不得在该区内及其以外1000米范围内兴建大水面的引水、蓄水工程 ,以防止城址的水位上升,危及地下古代遗存。”
保护规划方案中洛南里坊区绿地保护的远期目标则是:
“征用遗址保护区内所有机关单位、企事业单位和农业土地(含村庄),建立隋唐洛阳城里坊遗址公园;拆除所有与遗址无关的固定建筑和临时建筑,以彻底改善和治理环境风貌,使遗址保护区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整体环境风貌上完全和隋唐洛阳城协调,以完整保护隋唐洛阳城洛河南岸里坊遗址”;
“沿原里坊遗址内大街种植浅根灌木,展示里坊遗址路网格局”;
“以里坊为单位进行考古勘探与发掘。然后根据发掘结果,结合旅游,予以保护、展示”;
“保护、研究和展示隋唐洛阳城洛南里坊遗址区,在将来的洛阳市城市中心地带建设成一处占地20平方公里的充满古代文化内涵的遗址公园,使之成为人们休闲、娱乐和参观旅游的重要场所,成为净化现代化城市环境、促进市民健康的大绿洲”;
“有计划地开展隋唐洛阳城考古发掘、研究和文物保护、遗址展示工作,使隋唐洛阳城逐步成为中国研究隋唐历史的重要基地,成为中国隋唐文化的研究中心之一。”
由叶万松教授率先提出,并由规划编制小组完善的隋唐东都洛阳城洛南里坊区绿地保护的构想,今天己成为洛阳市城市发展的指导思想。
洛阳市第三期城市发展总体规划虽己通过论证,但仍未阻止城市建设对隋唐东都洛阳城的破坏。洛阳市领导集体对隋唐东都洛阳城遗址的保护进入理性化的认识,是在2000年洛阳龙门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动之后。市委书记李柏栓先生在接受《洛阳日报》采访时说,洛阳文化遗产的保护“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是古城(遗址)的保护”;对于隋唐东都城洛南里坊遗址总体绿地保护的规划,他予以充分的肯定。他说:“由于历史的原因,隋唐故城已经有很大部分被人为破坏了,仅留下洛南约20平方公里一处完整区域,对这里首先要进行合理科学的规划。以前我们总以为保护这处古城限制城市的发展,其实不然。根据我市的总体规划,将来隋唐故城以南,一直往西到辛店,都会发展为城市区,那时,洛阳将改变现在长条形的布局,基本呈方形。而隋唐故城就在市中心一带。我们的想法是在这里搞森林、草坪、花卉和观光农业,并有计划地进行保护性开发,使其成为一个遗址公园。试想,在市中心有一处这么大的绿地风景区,这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
叶万松先生率先提出的隋唐洛阳城洛河南岸20平方公里绿地保护的构想,其核心就是在城市化进程中避开旧城址易地建新城以保护文化遗产。这个构想实际上就是继承和发展了郑振铎、梁思成先生的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的城市建设中“古今兼顾、新旧两利”的理念。
(三)
2001年继任市委书记的孙善武①依然在东周王城、隋唐东都洛阳城遗址保护范围内大搞城市建设,形成了对文化遗产严重的破坏。
2002年7月,洛阳开始在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东周王城遗址内建设市中心广场——“河洛文化广场”,第一期工程占地4万余平方米,考古钻探了其中3万平方米,就发现了东周时期的墓葬400多座、车马坑(含马坑)36座。其中带墓道的大型贵族墓葬4座、中型贵族墓葬20余座、大型车马坑2座。在已发掘的10座马坑、车马坑中保存完好或基本完好的车马坑5座,其中一座长42米、宽7米的车马坑内埋葬26辆车、58匹马,组成浩浩荡荡的车队。车队中发现六马驾一车的考古遗存,根据《逸礼?王度记》“天子驾六马、诸侯驾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的记载,被确认为东周“天子驾六马”的考古遗存,东周天子的车队,于是又为该墓区为确认为东周王陵陵园遗址提供了文献和实物佐证,可以讲这是非常重大的考古发现。
广场发现的墓葬车马坑群引起洛阳有关方面专家的关注。9月中旬,在广场雕塑方案专家评审会上,与会的叶万松教授等强烈要求市委、市政府对广场总体设计方案重新论证;9月下旬,叶万松教授和原洛阳师范学院院长叶鹏教授共同策划,12位洛阳著名专家联名上书洛阳市委、市政府,要求重新审视原“河洛文化广场”设计方案;10月初,叶万松教授上书市委市政府和省文物局,全面提出原址整体保护墓葬、车马坑的方案的具体建议。但是这些建议并没有引起市主要领导人应有的重视。2002年12月12日,《大河报》头版头条和香港《文汇报》专版报道洛阳发现东周王陵和“天子驾六”车马坑消息并称该发现媲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于是又引起了国内和洛阳媒体连续20余天的追踪报导。出于对城市建设的关心,出于对文物保护的热心,一时间洛阳从市民到市政协委员、市领导决策层,都卷入到一场轰轰烈烈的大争论之中。
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孙善武建设现代化河洛广场的决心,2003年1目13日推土机、挖掘机进驻河洛广场考古工地,一场野蛮破坏东周王陵的违法事件便发生了。
“洛阳在毁什么?!”1月24日《中国文物报》大篇幅的报道揭露了河洛文化广场破坏文物违法事件真象。这引起了国家文物局、省政府的重视,也引起全国人大常委会毛昭晰等45位常委的关注,国务院温家宝总理在毛昭晰领衔的45位常委致温总理的信上作了批示。就是在这种强大政治和与论压力下,才使洛阳市主要领导孙善武不得不对自已的违法行为进行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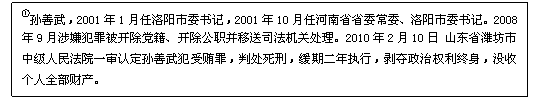
但事情的发展不是一般人所预料的。上级的调查组刚走不久,事件最终的结果是叶万松教授在2003年5日22日被免去了行政职务,而对于河洛广场文化遗产的保护方案,“形成了一个在中国大地处处可以见到得(的)文物向城市建设让步的妥协的方案,至此,文物考古部门在与政府的对抗中一败涂地。”
现在的河洛广场更名为东周王城广场,众多的遗迹,只有“天子驾六”车马坑被原地保存下來,成了博物馆,已经发掘清理出來的数个车马坑被迫回填,地下停车场挖空了“天子驾六”的周边,地上的一切都是现代化广场的样子,一切都显得没有王陵遗址的环境气氛。如今洛阳有关人士想把回填的4个车马坑、1个马坑清理出來,以扩大“天子驾六“车马坑博物馆的规模。由于车马坑回填时就存在争议,北京的某个考古学家在国家文物局专家论证会上认为“回填是最好的保护”,而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地质学家周昆叔教授、夏正楷教授,还有考古学家叶万松教授,则以“回填会产生新的物质置换”等科学理论为依据,认为回填无疑是毁坏,所以直到现在,没有一个考古学家敢再次清理回填的车马坑。
2000年10月,河洛广场的考古发掘工作还在进行时,叶万松教授就分别上书洛阳市委和河南省文物局,全面提出原址整体保护河洛广场东周王陵的意见《“河洛文化广场”与东周王城——关于筹建“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博物馆暨东周王城(王陵区)遗址广场(公园)”的建议》,其具体设想主要有以下几条:
1、继续对东侧未拆迁的部分进行拆迁,对未钻探的部分进行钻探,以整体了解古文化遗迹分布;
2、广场周边种植高大树木隔离带,以使广场和周边的现代化建筑隔离,以阻挡人们视线的办法达到协调广场和周边的环境的目的;
3、广场内部采用草坪绿化以营造墓地圹野气氛,在草坪中辟出幽曲小径,供参观者使用;
4、展示车马坑,对已经发掘的车马坑进行修复加固,加盖玻璃罩进行展示,对已发掘的马坑进行复位,修复加固,加盖玻璃罩进行展示。未发掘的几座车马坑和以后钻探发现的车马坑,或进行发掘、修复加固,加盖玻璃罩进行展示,或暂不发掘,以待广场建成后对观众作展示性考古发掘。每座马坑和车马坑都要在地面做出精美说明标志牌;
6、对已经发掘的墓葬,在地面上作投影展示,并设计精美的说明标志牌,就墓葬编号、尺寸、形制、方向、葬式、葬具、随葬品以及发掘时间、发掘单位作出说明标志并附墓葬平面图、剖面图和发掘照片。对未发掘的墓葬或可作投影展示,并制作说明牌,说明墓葬编号。有计划地保留几座墓葬作结构展示,如积石积炭墓,可保留墓室周边的积石积炭,并于修复加固,加盖玻璃罩进行展示;
7、在广场合适位置建造陈列馆和遗址广场眺望平台。建造陈列馆,主要介绍东周王城这处重要古代都城遗址,陈列东周王城50年来考古发掘成果和文物,并在其中辟出一室专门介绍广场内出土文物。建造眺望平台,使参观者可登高眺望遗址广场全景。
叶万松教授关于筹建“遗址广场”实际上就是筹建遗址公园的建议,当时就被河南省文物局孙英明副局长称之为“河洛广场文物保护大手笔”。现在重温他的这个建议,方知叶万松教授关于保护文化遗产的真知灼见。设想当年这个建议若能得到实施,恐怕现在也不至于有人后悔当年了!
(四)
当年除了郑振铎先生为洛阳东周王城文化遗产保护做出贡献外,还有夏鼐先生,20世纪80年代初,在他的力主之下,洛阳首阳山电厂改变规划方案,从而保护了偃师商城遗址。郑振铎先生是福建人,生于浙江温州,是我国20世纪30年代文化巨匠,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奠基者和政策制订者,夏鼐先生是浙江温州人,新中国考古事业的领导者、奠基者,他们都是大人物。叶万松先生亦是浙江温州人,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一辈子在洛阳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主持洛阳考古发掘达15年之久,他虽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他为洛阳、为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作出了贡献。早在1982年,他就与余扶危先生一起,创造了被国家文物局誉为地下文物保护“洛阳方式”的考古发掘报批制度,为我国《文物保护法》考古发掘报批制度的制订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名闻全国文物考古学界。
由于他长期主持东周王城和隋唐东都洛阳城的考古工作,使他身陷城市建设与文化遗址保护的矛盾之中,他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一片忠诚使他常常与市某些领导意见相佐。如1996年,洛阳市政府决定在隋唐东都城洛南里坊遗址上建设一座大型的公园设施——“万国国花园”,由北京农业大学承担设计任务并已完成。在市规划局组织的审批会议上,出席会议的叶万松教授首先提出反对意见:“这个设计方案是一流水平的,只可惜是选址在隋唐洛阳城内。我们认为,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内设计建设如此大型工程设施,必须慎之又慎,园内挖掘大型水面既会大面积破坏遗址,又可能造成地下水位上升,对整个隋唐东都城外郭城遗址形成破坏,所以我们不同意把该工程放置在隋唐城内。如果市领导执意在隋唐城内建设,根据《文物法》规定请市领导与国家文物局协商”。由于遭到在洛阳工作的考古专家们的反对,在会议之后,市长只好亲自率领市规划局、市文物局领导赴京向国家文物局汇报,国家文物局特意组织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进行论证,结果在隋唐东都城保护范围内筹建“万国国花园”的建设方案还是被否决了。
他主持洛阳考古发掘工作的十多年來,就文化遗产保护与市领导发生矛盾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尽管他学术成绩卓著,名闻全国文物考古学界,是洛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的顾问,洛阳古都学会会长、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副会长、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但他既不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学者,也不是“省管优秀专家”,甚至连“洛阳市优秀专家”都不是,因为他身处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矛盾中。1995年洛阳市城市发展总体规划通过论证,叶万松就依据这个规划保护起隋唐东都洛阳城里坊遗址來了,二年多來就不申报配合建设考古发掘项目,使得洛阳市在隋唐城保护范围内的城市建设工程严重受阻。1997年九、十月间,市主要领导人派员來疏通,被叶万松婉言拒绝。就是在这大背景下,1997年12月,洛阳社会科学联合会报审叶万松教授为省政协委员的意见被否决了,紧接着叶万松便遭到了诬告,1998年1月被洛阳市老城区检察院反贪局以受贿罪立案审查,并被采取了“监视居住”、“取保侯审”等法律手段。经过长达二年的严格的司法审查,没有查出叶万松任何贪污、受贿经济问题,最后是撤案、恢复名誉,恢复职务,还了叶万松一个清白,连办案的反贪局长也不得不承认“叶万松是党的好干部”。
经过1998~1999近二年冤案的磨难,叶万松教授并没有在文化遗产保护的道路上退却,而是更加地坚定。2002~2003年,叶万松教授还是为保护洛阳河洛广场东周王陵(车马坑)冲锋陷阵,到最后几乎是只身孤胆奋战。充分表现了他对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赤胆忠心。
如果说,那些供职中央机构和高校学府的专家学者,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批评某些地方官员破坏文化遗产的行径,并饱受社会赞许的话,那么,叶万松教授,作为供职于基层,工作在文化遗产保护第一线的考古学家,身处城市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矛盾的风头浪尖,他的保护文化遗产的言论和行动,总是让他陷入困境,遭受磨难,甚至于迫害。叶万松教授并没有因为身受不正公的待遇,而动摇过保护文化遗产的信仰,十几年來,他为古都洛阳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这种始终不渝地、不屈不挠地奋斗,这正是叶万松教授人格的伟大所在。
回顾洛阳市文化遗产保护的历史,无论是郑振铎先生、夏鼐先生,还是叶万松先生,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他们的在城市化进程中文化遗产保护思想都坚持文化遗产原址整体保护,城市建设应尽可能避开文化遗产的原则。应该认为,叶万松教授是我国少有的几个自觉地践行着在城市化进程中考古发掘必须注重遗址科学保护原则的考古学家。叶万松和余扶危先生还是我国第一个提出“(考古)发掘须经主管当局事先许可” ,並率先在本工作区域内建立考古发掘报批制度,对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立法有着重大贡献的考古学家。
叶万松教授退休后,就淡出文物考古学界,转入古都学界,热心参与中国古都学会工作,主编《中国古都系列丛书》。但他依然关心着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潜心总结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与教训,探索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这次他在中国古都学会大同年会上发表的论文《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关系的哲学思考》,洋洋三万余字,就是他近年來研究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重要成果。从他发表的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仅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家,还是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家。
叶万松教授今年八月从大同回來后,在电话里就很兴奋地对我谈了大同市领导集体在城市建设中创造的保护文化遗产的新思维和新模式,他还把这种模式称之为“城市建设‘大同模式’”;同时他还告诉我,他在大同就有自己“生不逢时,话不择地”的苍凉之感,说自己在洛阳工作了三十多年,就没有遇到像大同耿彦波那样关心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好书记、好市长而感到遗憾。
我今天写这篇文章,一是回忆郑振铎先生、叶万松先生为保护洛阳文化遗产所做的贡献,算是一种历史的记念。二是告诉大同文物考古学界的同仁,你们有了一个关心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市领导集体,是值得庆贺的。要爱惜这个时代赋予的大好机遇,努力工作,把大同的考古事业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推向新阶段,把大同建成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旅游城市与文化城市。
参考文献:
1.河南省科技大学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组:《洛阳城市发展与文物保护的经验与教训研究》,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资助项目(2003001)
2.赵丽等:《赤子情》,《莽原》1994年第1期,莽原杂志社出版;
3.2001年洛阳市文物局上报河南省文物局的《隋唐洛阳城遗址保护规划(报审稿)》
4.《洛阳日报》2000年12月8日第一版
5.《高尔夫球场侵蚀隋唐古城遗址》,《第一财经日报》 2006年9月13日A8版
6.7.考古门下一走狗:《感叹考古的环境》,2003年4月19日,国学论坛
8.http://bbs.guoxue.com/viewthread.php?tid=145110&extra=&page=2
9.于世茂:《“‘天子驾六’动洛城”系列之四·“沧海桑田”今何在》,《大河报》2004年8月26日B16版
10.叶万松:《洛阳的选择:“河洛文化广场”与“东周王城”》,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编《人大建设》2003年第1期
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适用于考古发掘的国际原则的建议》(1956年),《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文物出版社2007年40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