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要:隋唐时期的云州(治今山西大同市),属“边州”之地,既是边防前沿的军政重镇,也是“阴山防线”的重要地段。作为自然地理上农、牧经济的过渡地带,这里又是多民族杂居融合、迁徙去留比较频繁的地区,因而也是“多事”之区。在杨隋与李唐前期,雄踞阴山内外、大漠南北的突厥、薛延陀汗国,曾多次南下侵扰云州及其相邻州县,严重威胁着北疆安全与边地百姓的生产生活秩序。本文举要述论隋朝与唐代前期云州的军政建置、重大战事和民族迁徙等,从而显示这一历史时期云州政治、军事、民族风云的基本面貌。
关键词:云州;突厥;唐前期;阴山防线;河东节度使
隋唐时期的云州(治今山西大同市),在地理空间位置上属于“边州”之地,既是边防前沿的军政重镇,也是构成国防之“阴山防线”的重要地段。在自然与人文地理上,这里属于农、牧经济的过渡地带,是多民族杂居融合、迁徙去留比较频繁的地区,因而也是“多事”之区。在隋朝与唐代前期,雄踞阴山内外、大漠南北的突厥、薛延陀、后突厥汗国,曾多次南下侵扰云州及其相邻州县,严重威胁着北疆安全与边地百姓的生产生活秩序。
本文举要述论隋朝与唐代前期云州的军政建置、重大战事和民族迁徙等,从而显示这一历史时期云州政治、军事、民族风云的基本面貌。
一、唐代云州的行政建置沿革
唐代河东道北部的云州(今山西大同市),在隋朝为马邑郡(今山西朔州市)云内县。马邑郡统辖4县:善阳、神武、云内、开阳;共有户口4674。[1] 若平均计算,则云内县有居民1000户左右。
隋末唐初,天下动乱,群雄并起。马邑郡下的军府将领刘武周起兵反隋,自称皇帝,北附突厥汗国,在代北地区建立了割据政权。
李唐新朝建立后,高祖武德四年(623),平定刘武周;六年(625),于云内置北恒州,但仅一年时间,即告废弃。直至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自朔州北定襄城(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移云州及定襄县置于此。[高宗]永淳元年(682),为贼(后突厥)所破,因废。乃移百姓于朔州。[玄宗]开元二十年(732),复为云州”。[2]
唐代的云州,与忻、代、岚、朔、蔚州,皆为“边州”,[3]即北部边疆之地,是国防的前沿阵线,也是游牧族类迁徙去留比较频繁的地带——正州(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与羁縻府州(中央政府间接统治)交错分布,虽然地域广大,但各“边州”的编户百姓人数并不多(见下表)。
唐代云州的州境东西170里,南北490里,仅领有云中一县(初名定襄,开元二十年复置时改为云中)。而云州的行政建置曾有中断,其领县少、民户寡等情形,与地处河东道最北部、属边防前沿等空间位置,有直接关系。
(表1) 隋唐河东道北部“边州”编户简表
|
户口 州名·县数
|
隋朝《隋·志》
|
唐初《旧·志》
|
开元《元和志》
|
天宝初《通典·州郡》
|
天宝十一载《旧·志》
|
元和《元和志》
|
|
忻州·2
|
----
|
户4987口17130
|
户14338乡28
|
户15038口77930
|
户14806口82032
|
户4204乡29
|
|
岚州·3/4
|
户24427县3
|
户2842口11541
|
户17026乡22
|
户15680口72206
|
户16748口84006
|
户6382乡40
|
|
代州·5
|
户42502县5
|
户9259口36234
|
户15077乡28
|
户21020口101450
|
户21280口100350
|
户2120乡40
|
|
朔州·1/2
|
户4674县4
|
户1257口4913
|
户6020乡13
|
户6300口25800
|
户5493口24533
|
户729乡16
|
|
云州·1
|
----
|
户73口561
|
户3169乡7
|
户3160口7930
|
?
|
户(?)乡7
|
|
蔚州·2/3
|
----
|
户942口3748
|
户4887乡11
|
户4610口18200
|
户5052口20985
|
户1563乡12
|
|
说明:隋大业(605—618)中,河东太原以北地区有楼烦、雁门、马邑三郡。
|
二、云州四达交通路线[4]
从历史军事地理角度观察,一个地方(或地区)的战术与战略地位价值,与其山河形势、交通状况的难易程度密切相关,尤其是丘陵、山地、大高原等高下崎岖、交通困难的地区,更是如此。而沟谷通道、山岭隘口、江河津渡等,则具有战略上的控制意义。
今大同盆地,位于山西省北部、内外长城之间,为桑干河盆地的西部(东部为河北宣化盆地)。桑干盆地为河北平原和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自古以来农、牧业发达。大同盆地由桑干河及其支流御河(南北流向)等切割黄土高原并冲积而成,海拔高度1100米左右。盆地南倚恒山(东北–西南走向,绵延150公里,为桑干河与滹沱河的分水岭,是南北交通上的天然阻障),西接管涔山(稍呈东北–西南走向),桑干河(西南–东北流向)流贯其间。
1、南北交通主线
隋唐时期,由太原府向正北行通往边塞之路线,经过云州。其具体经行为:出太原府正北行180里至忻州(今忻州市),又北行160里至代州(今代县),又西北行30里至雁门关,又直北行略循今黄水河(桑干河南源)而下至桑乾镇(隋时所筑。今应县西北),又稍北行至黄花堆(今怀仁县南约30里),又东北行50里至神堆栅,又东北行50里至云州(今大同市)。总里程为700里。
据中唐宰相杜佑记载:由云州向西北行160里,有却蕃栅(今内蒙丰镇市西北);向北行300里到长城(即北魏长城。今内蒙集宁市以北)蕃界;向东北行到阳阿谷蕃界340里。即进入游牧部族的活动地区。[5]按:杜佑所记应是盛唐时的情形,其“却蕃栅”即是曾经驻军守边之地;而“长城蕃界”、“阳阿谷蕃界”,即是唐朝边防的实际控制线。
2、东西交通线
由云州向西行,通往关内道北部的河套地区(今内蒙阴山之南);向东行通往河北道北部的妫州(今河北怀来县东南)、幽州(今北京市西南)方向。
由云州西行50里,有东尖谷;西行180里,有静边军(今山西右玉县西北右玉城);[6]由静边军西北行120里至单于都护府(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土城子)。[7]
云州城东北60里有牛皮关;又有青坡道、阴山道,皆为出兵之要道。[8]
由云州东至河北道幽州方向,里程约有700里。其经行路线:东北行120里至清塞军(今山西阳高县南),又东北行60里至天成军(今山西天镇县),又东北行90里至纳降守捉城(唐末置怀安县。今河北怀安县东南),又略东南行220里至妫州(今河北怀来东南),又东南210至幽州(今北京西南)。
又由天成军(今山西天镇)东南行180里至蔚州(今河北蔚县),折东北行250里亦至妫州。[9]
三、重大战事与边防建设举要
1、隋仁寿元年(601)恒安镇之战[10]
隋文帝开皇十九年(599)十月,册封东突厥突利可汗为启民可汗,于阴山之南的河套筑大利城(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使居之。当时,西突厥达头可汗控制了漠北广大地区,频繁南下侵掠。开皇二十年(600)时,代州行军总管韩洪(名将韩擒虎之弟)、朔州总管李药王(韩洪外甥、唐名将李靖之兄)与蔚州刺史刘隆等,统领步骑兵万余人,驻守于恒安(今大同市),防御突厥南侵。
仁寿元年(601)正月,达头可汗率10万骑,大举南侵,驻守恒安镇的隋军首当其冲。由于兵力悬殊,韩洪、李药王、刘隆等将率军四面拼杀,皆身被创伤,而突厥军悉众围攻,箭如雨下,情势十分危急。韩洪乃向突厥诈称讲和,待其攻势稍缓,即率余部冲围面出。隋军死伤大半,杀伤敌军亦倍。
这是一场极为惨烈的血战。时隔6年之后的大业三年(607)四月,炀帝出塞北巡至恒安,见到隋军阵亡将士的尸骨仍暴露于荒野,悯然伤感,下令收葬尸骨,命五郡沙门为设佛供,超度亡灵。
2、隋末唐初刘武周、苑君璋割据代北(617–627)[11]
隋末天下动乱,群雄并起。大业十三年(617)二月,马邑郡(今朔县)军府鹰扬郎将刘武周起兵反隋,攻占雁门(今代县)、楼烦(今静乐)、定襄(今内蒙和林格尔)等郡,投靠东突厥汗国,自称皇帝,在代北建立起割据政权,并多次南侵太原及其以南。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刘武周被突厥杀死,其妹婿苑君璋统领余众。六年(623)七月,苑君璋引突厥兵进攻马邑,被唐将李高迁等击败于腊河谷(今朔县东北)。十二月,苑君璋再攻马邑,陷城。其部将进言:“恒安之地,王者旧都,山川形胜,足为险固。”苑君璋纳其言,遂退保恒安镇(今大同市)。
至唐太宗贞观元年(627)五月,苑君璋率众来隆。而恒安之地遂为突厥所占据。
3、初唐时期云州之置废[12]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冬至次年三月,唐军10万余众,岔道出击,以犁庭扫穴之势,击灭东突厥汗国,将阴山至大漠的广阔地域收入版图。随后,将突厥降户10万余人安置在河北、河东、关内三道北部地带,以其部落设置羁縻府州,推行“以夷制夷”的间接统治。这就是贞观十四年(670)之前,云州之地无正州、县建置(中央政府直控统治)的局势背景。
贞观十三年(639)七月,诏令安置在关内道黄河以南诸州的突厥及诸胡部落,皆渡河还居其漠南旧地,立阿史那思摩(赐姓李)为可汗。十五年(641),李思摩帅10余万部众、胜兵9万、马9万匹渡河,建牙于故定襄城(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
于此同时,唐朝“自朔州(今朔县)北定襄城移云州及定襄县”于恒安镇安置,即置云州及郭下定襄县(开元中改名云中县)。
按:当时,漠北的薛延陀汗国已经坐大,成为继东突厥汗国之后的又一军事强权势力。唐朝下令李思摩率众北徙,就是想要形成突厥居漠南,薛延陀居漠北,各守土境,不得逾越,从而长保边塞的地缘军政格局。
再从军事防御的角度观察,云州未置之前,从代州(今代县)以北直至阴山,数百里纵深地带无正州建置。漠北薛延陀坐大之后,虎视眈眈,不时南下抄掠突厥部落。而李思摩畏惧薛延陀之强盛,不愿北徙旧地。是故唐朝于此时设置云州,充实边防之地,亦为李思摩之声援。按:云州地处边防前沿,在新设行政建置的同时,必定也要调兵驻防。然无史载可据,只能以情势理性作约略推断。而上述唐朝的战略计划,直到贞观二十年(646)六月,击灭薛延陀汗国之后,才基本实现。取代薛延陀又复雄强漠北的回纥汗国,则与唐朝保持了政治和好关系。
到了唐高宗咸亨(670—674)中,漠北突厥部落南来归降者,散处于关内、河东道北部的丰、胜、灵、夏、朔、代六州,称“六州降户”。按:当时,云州尚未重置,凡提及朔、代两州,即包括了云州——不可能空其地而不安置突厥部落。但是,好景不太长,便被突厥贵州的复国反叛活动打断了。
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十月,关内道北部单于大都护府(内蒙和林格尔西北)所辖的突厥部落24州酋长相继叛乱,众至数十万众,动乱波及关内、河东、河北三道北部。唐军最多时出动30万众,直至开耀元年(681)七月,才基本平息了这场大暴乱。但突厥残部的复国活动并未绝迹,且越来越强,至垂拱二年(686),骨咄禄建立后突厥汗国,不复为唐朝臣属。而唐朝北疆局势由此日趋恶化,直至玄宗朝才开始逐渐扭转局势,重新控制了阴山防线的主动权。
正是由于漠南突厥降户反叛,导致了永淳元年(682),云州被残破,州县见废,百姓南迁于朔州安置的恶果。唐朝“亡羊补牢”,在云州等地设置驻军镇防,以有效控制阴山之南的广大地区。
调露二年(680。八月改元永隆)七月,突厥围攻云州,被唐军击退。由于突厥在军事上属于骑兵游动作战方式,而唐朝“边州”必须据地自守,平叛总指挥、行军大总管裴行俭遂奏请于云中设置守捉(边防驻军编制单位),驻兵7700人,战马2000匹;在朔州(治善阳。今朔县)东面30里设置神武军(改原大武军而设),驻兵9500人,战马5500匹。当时,突厥叛乱侵寇的主要方向是在关内道北部的河套地区,而由代州出雁门关西北行至朔州,再西北行至单于都护府,是一条交通干线,也是突厥进犯常取之道,故神武军的兵力较多。按:史书记载的这一军、一守捉所管兵马数字,应是叛乱平息之后的常驻兵力。
而云州的再次设置,是在盛唐开元二十年(732),相隔时间长达50余年——正是后突厥复国至最强盛阶段,也是唐朝北疆羁縻府州体制开始解体时期。
后突厥复国与北疆军政局势全面恶化,是这一时期李唐帝国面临的突出而严峻挑战。从高宗后期到玄宗即位的30年间,唐朝的中枢政局多次发生重大变故——武太后改唐为周、数易皇帝和七次宫廷政变,直接影响了对后突厥反叛复国活动的军事征讨和政治抚辑。直到玄宗即位后,才出现了上下精诚,同仇敌忾的政治景象,在不断加强“阴山防线”建设的过程中,逐渐扭转了被动守御的军事态势。
4、盛唐河东节度使防区的建设过程
唐代北方边疆的国防阵线长达2万余里,其中最重要的地段就是“阴山防线”。从地理空间上来看,阴山防线应包括今贺兰山、阴山与黄河河套地区。从当时的行政区划上看,应包括关内道北部的单于、安北两大都护府和丰、胜、灵、会州以及河东道北部的蔚、云、朔、代、岚、忻诸州;在军事地理上,阴山防线是指上述诸“边州”境内的军、守捉(包括镇、戍、烽堠)和州县城邑组成的彼此连接,相互支援的军防体系,其中军事城镇是维持边防空间秩序的“支撑框架”和决定因素。而军事城镇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屯田又是极重要的因素。正所谓“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器),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13]
自圣历元年(698)以后,凡向太原以北方向出兵抵御突厥者,多以“天兵军”命名、设“行军大总管”总其军事。按:“行军”指野战出征,属临时性质。而设置“××道节度使”之后,便转为地方镇守性质,有了固定的防区和兵力配置。诸道节度使左右应援,能够及时、就近应付大规模的边疆突发事变和战争。
按:盛唐时期,于边疆地区设置十道节度、经略使(节镇、军区),遏制四夷。河东道节度使防区,与西邻的关内道朔方节度使(治今宁夏吴忠市),互为犄角,共同防御漠北的后突厥汗国。
玄宗开元五年(717)七月,置天兵军于太原府,集中兵力8万人,以镇抚突厥降户部落,由并州长史张嘉贞充天兵军大使。十一年(723)三月改为太原已北诸军节度使;十八年(730)十二月以后为河东节度使。
开元四年(716)六月,后突厥默啜可汗被漠北敕勒(铁勒)部落袭杀,传首来献。拔曳固、回纥、同罗、霫、仆固等部落皆南来归降,被安置于大武军(后改名大同军,在朔州东30里)以北地区(即朔、云、蔚州境地)。
六年(718)六月,张嘉贞将蔚州(今山西灵丘)境内的横野军,移于恒山之北的大安城(今河北蔚县),屯汉兵3万,以为铁勒诸部之援。诸部酋长所统之马骑(骑兵)共有6800人。
十五年(727)九月,唐朝于关内道北部的西受降城(今内蒙五原西北黄河故道北岸)开设“互市”,允许后突厥来进行绢马交易。由此以后,后突厥对阴山方面侵扰逐渐稀少,盖因其内部分裂,势力大削之故也。
自开元二十八(740)至天宝五载(746),名将王忠嗣先后担任河东、朔方节帅,在任期间,曾大力强化阴山防线建设,向外开拓数百里之地。“开元之末,拥旄汾代;天宝之始,兼统朔方。……公始以马邑镇军守在代北,外襟带以自隘,弃奔冲而蹙国。河东,乃城大同于云中,徙清塞、横野,张吾左翼;朔方,则并受降为振武,筑静边、云内,直彼獯虏。……”[14] 按:王忠嗣曾任大同军使,后又掌控河东、朔方两节镇,遂从阴山防线全局着眼,在频繁派兵出击突厥部落的同时,加强军事防御工程体系的建设。依据史载,其具体措置如下。
(1)于云州新筑军城,将朔州马邑县的大同军北移来驻防。这样以来,驻在云州的兵力,合计为17200人,马7500匹。占河东军镇总兵力的26﹪、军马的51﹪,成为名副其实的边防重镇。
(2)将蔚州旧治灵丘西面的清塞守捉,北迁至云州东北(今山西阳高)驻防。
(3)新筑静边军城(今山西右玉县西北)。但兵力情况未见史载。
(4)将东受降城(兵7000人,马1700匹)与单于都护府城(今内蒙和林格尔西北)的振武军(兵9000人,马1000匹)合并,即兵力集中,以便机动使用,同时将防区向北推进。
(5)徙“横野”(军)一事,史载分歧,多有疑义,或为徙“楼烦”(樓烦)之讹误。以下试作考辩。一孔之见,敬祈学界同仁指教。
①据《新唐书·地理三》:云州境地有云中、楼烦二守捉。岚州有守捉兵;静乐县(今县)北有管涔山、楼烦关(今山西宁武县东北阳方口)。由此推测,“楼烦守捉”原驻楼烦关;天宝初,王忠嗣将此守捉北移到云州境地(或即云州东北的天成军)—— 如此,则与所谓“张吾左翼”相符合。
②王忠嗣兼统河东、朔方两节帅,以天成军、清塞守捉、云中守捉、大同军、静边军、振武军共同构成一条东西连接的防线;而楼烦关、大同军旧地、清塞守捉旧地皆在此新防线之南。如此,正与“当要害地开拓旧城,或自创新,斥(开拓)地各数百里”[15] 的史载相吻合。
③王忠嗣当年因为遭到权相李林甫的谗害而蒙受冤屈,被贬降之后,于天宝八年(749)45岁的盛年暴卒。至肃宗宝应元年(762)昭冤,追赠兵部尚书。时任宰相的元载(王忠嗣女婿[16])为其撰写碑文,颂扬功烈。上距忠嗣身亡已10余年矣,追叙其生前功勋,故或稍有差池。也有可能是后世传抄、刊刻时的讹误。
盛唐河东节度使的驻防布局如下表。
|
名称 治所(今地)
|
兵马数
|
建置事略
|
盛唐屯田数
|
|
天兵军 治太原府城(今太原市西南)
|
兵20000人(30000人)马5500匹
|
开元五年(717)七月置。
|
1屯(?)
|
|
忻州 治秀容县(今忻州市)
|
兵7800人
|
有军府4:秀容、高城、漳源、定襄。有守捉兵。
|
——
|
|
岚州 治宜芳县(今岚县北)
|
兵3000人
|
有军府1:岚山。有守捉兵。
|
岚州1屯
|
|
代州 治雁门县(今代县)
|
兵4000人
|
有军府3:五台、东冶、雁门。有守捉兵。
|
——
|
|
岢岚军 岚州北岚谷县(今苛岚)
|
兵1000人
|
? 唐初武德时为镇;高宗永淳二年(683)改为栅,隶平狄军。长安三年(703),李迥秀改为军。中宗景龙(707—709)中,张仁亶移其军于朔方,留1000人充守捉,属大武军。开元十二年(724),崔隐甫又置军;十五年(727),李暠又废为镇。开元二十六年之前又改为军。
|
——
|
|
大同军 朔州东30里(今朔县东)
|
兵9500人 马5500匹
|
? 本大武军,在朔州东30里。高宗调露二年(680),裴行俭改为神武军;约永淳二年(683)前改为平狄军;大足元年(701)五月十八日,改为大武军;玄宗开元十一年(723)三月四日期,改为大同军。玄宗天宝初,王忠嗣移大同军于云州驻守。
|
大同军40屯 朔州3屯
|
|
横野军
|
兵7800人(3000人)马1800匹
|
垂拱(685)中初置在飞狐县(今河东涞源),后移于蔚州(今山西灵丘)。开元六年(718)二月,张嘉贞移于恒山北古代郡大安城南,管兵7800人,以为九姓铁勒之援。
|
横野军42屯 蔚州3屯
|
|
云中守捉
|
兵7700人 马2000匹
|
高宗调露中,裴行俭破突厥置。
|
云州37屯
|
|
清塞军(今阳高县)
|
?
|
本清塞守捉,在蔚州西。天宝初,王忠嗣移于云州东北驻守。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四月置为军。
|
——
|
|
天安军(今天镇县)
|
?
|
?
|
——
|
|
代北军
|
?
|
代宗永泰元年(765)置。
|
——
|
(表2) 盛唐河东道节度使驻防简表
按:查阅唐代史籍,所载诸军、守捉的兵力数量略有异同,经综合比较,可以作出基本判断,这应是反映着不同时段兵力调整的具体情形。亦列表附后,以便读者诸君观览比较。
(表3) 盛唐河东道节度使诸守捉兵力异同简表
|
史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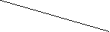
军、守捉
|
《通 典》
|
《元和志》
|
《旧·志》
|
《通 鉴》
|
|
天兵军
|
兵20000马5500
|
兵20000马5500
|
兵30000马5500
|
兵30000马5500
|
|
大同军
|
兵9500马5500
|
兵9500马5500
|
兵9500马5500
|
兵9500马5500
|
|
横野军
|
兵7800马1800
|
兵7800马1800
|
兵3000马1800
|
兵3000马1800
|
|
岢岚军
|
兵1000
|
兵1000
|
兵1000
|
兵1000
|
|
云中守捉
|
兵7700马1200
|
兵7700马1200
|
兵7700马2000
|
兵7700马2000
|
|
忻 州
|
兵3000
|
兵3000
|
兵7800
|
兵7800
|
|
代 州
|
兵4000
|
兵4000
|
兵4000
|
兵4000
|
|
岚 州
|
兵3000
|
兵3000
|
兵3000
|
兵3000
|
|
合计
|
兵56000马14000
|
兵56000马14000
|
兵66000马14800
|
兵66000马14800
|
|
说明:《通典·州郡典》是以天宝地理为据;《元和郡县图志》记有盛唐、元和户口;《旧唐书·地理志》以天宝十一载(752)地理为据;《新唐书·地理志》记有天宝户口,叙沿革至晚唐。
|
四、简短结语
在唐朝前期(以“安史之乱”为时界),先后有东突厥、薛延陀、后突厥汗国称雄大漠南北,屡屡侵寇阴山之南的农耕地区,大肆抢掠人口、牲畜和财物。而河东道云州之境,首当敌冲,曾致州县残破,百姓流离;健儿捐躯,白骨曝野;边陲不宁,朝廷旰食。赖有干臣运筹,托长城而筑垒,守兵要而捍御。今人览史,良多感慨,洒清酒以祭英魂,赋史文颂扬功烈。秦汉明月,隋唐边关,古迹犹存,汗青当继。
?[参考文献]
[1]《隋书·地理中》,第853页。
[2]《旧唐书·地理二》,第1487—1488页。
[3]《唐六典·户部》,第73页。
[4]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五·太原北塞交通诸道》;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五》
[5][6]《通典·州郡九》,第4744页。
[7]《元和郡县图志》卷4,第108页。
[8]《新唐书·地理三》,第1006—1007页。
[9]《元和郡县志》卷14,第404页。
[10]《隋书》卷3《炀帝纪》、卷52《韩洪传》、卷65《李景传》。
[11]《旧唐书》卷55《刘武周传》;《通鉴》卷190,第5969页;卷192,第6035页。
[12]《旧唐书·地理二》,第1488页;同书《突厥传》。
[13]《管子·权修篇》。
[14]《全唐文》卷369元载《王忠嗣碑》,第1658—1660页。
[15]《旧唐书·王忠嗣传》,第3199页。
[16]《旧唐书·元载传》,第3414页。
|







